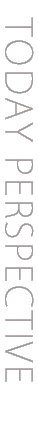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中国小说:焦虑与问题
──与张庆国对话
李敬泽
时间:2006年11月17日下午两点
地点:北京中国文联大楼旁某餐馆
谈话人:李敬泽、张庆国
李:文学有庸俗的一面,就像日常生活,天下再大的美女,也要排泄,没办法,文学肯定也有这一面,谈版税也不能客气。但文学是有自己的价值观的,现在要说的是,我们是不是全面失守了?
张:是不是价值观改变了?或者弄浑了?
李:对。
张:好的迹象就没有?作家们就没有写出令人兴奋的作品?
李:即使在如此浮躁的局面下,坚持艺术信念,决心写出好作品的人还是有的。我们今天是从总体上谈问题,那么,好的小说家肯定是有,正如中国的诗,绝不像媒体所说的那样一塌糊涂,满目黑暗,不是那样,好诗是有的,还有非常好的诗人,你们云南的于坚就是非常好的诗人。所以前几天两个记者问起诗的问题,我说,我希望你们媒体拿出和发现坏诗人一样的热情来发现好诗人。坏诗人是发现不完的,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坏的都占大多数,唐诗五万首,都是好的?不可能,伟大灿烂的唐诗,也就是两三千首吧,其它也不过就是垃圾,这是太正常的事了。现在,媒体、大众,比较热衷于发现诗坏到什么样,小说坏到什么样。坏到什么样?你要真去找,多的是。好的东西从来就是稀少的。
张:除了时代的复杂和迷乱、作家思想的迷乱、市场什么的影响等等,好像还有别的问题?就是说,除了大问题和大毛病,好像还有小问题,具体问题上也有出错的地方?是什么问题呢?耐心不足?什么叫有耐心?
李:有时候,小说写不好,问题确实就是没有耐心,以为可以快,人人都想找到灵丹妙药,一副药下去,就不断加印,电视就改编,就红了。人人在找灵丹妙药,我看到现在也没有找着,有时候只是碰上了,事先号脉也号不出来。但是,我相信一条,活儿做到那儿了,会有结果的。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很多长篇小说,作家放进去的精力、能力、时间都严重不足,行家一眼就看出来了。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他有多了不起,多伟大,我也不觉得,但是,我读了以后,就觉得写这个长篇,他一定做了很长时间的周密准备。他写的是伊斯兰文化里的细密画,好比你写一本北宋宫廷画院的小说,可是你看他掌握的细节多么丰沛,那种消化工作,绝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完事的。这样的工作方式,这样的工作精神,中国作家现在很少。
小说说起来可以一直说到人类精神上去,玄虚无比,可也是一个技术性的活儿,活儿没练好,你有多少高远的大话也不行。中国一年一千部长篇,我看艺术上及格的不超过二十部,这二十部里大部分也就是及格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谈这个谈那个,精神啊立场啊,伟大传统啊,开什么玩笑?就这两刷子配做伟大传统的传人吗?肯定的,现在小说的普遍艺术水准比八十年代是强多了,但是绝大部分小说艺术上是不过关的,原因呢,都是赖读者,说读者不喜欢好的活儿,我不相信。读者并非像作家想象的那么傻。你注意到一个问题没有?以前,中国和外国的畅销书是不同步的,纽约的畅销书,拿到中国卖不动,可能也就卖个三五千本,现在,渐渐的,这个现象在改变。你看今年卖得很火的书《追风筝的人》、《我的名字叫红》,几乎与国际市场同步,卖得很火。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能有朝一日中国的文学读者都在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的书而不读你们的书。这固然有跨国资本的强大力量在起作用,但是咱们最好也检讨一下自己的本事。说实在的,咱们很多自我感觉甚好的作家,基本艺术功力连人家一个通俗小说家也赶不上,还老把读者当傻瓜。读者不是傻瓜,读者要想看不动脑子的,想看俗的蠢的,他有比文学多得多的选择。既然这个读者肯花钱买一本小说,买一部文学作品,那么他一定是别有期待的,这个期待最好不要以后都被《纽约时报》畅销书去满足。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的长篇小说,你去看吧,基本上都是全知视角。全知视角是最伟大的视角,但是,更可能最愚蠢最懒惰的视角。在我们这儿恐怕情况就是后者,你懒得费那份心,我这个故事要从一个特殊角度,一个受限制的角度、有难度的角度去讲述,去展现出世界的独特面貌,你根本不想费那个力,坐下来,从头开讲,照直走,驾驶推土机一样,往下推,把这个故事讲完拉倒,这就是丧失艺术志向。
现代小说的基本问题,首先就是视角。在这个时代,小说家尤其应该注意的就是你与世界的关系。作家是在大街上走?还是像一个秘密活动分子,去寻找自己的小径和密道?这是最基本的艺术信念问题。
张:秘密活动份子这个比喻很绝妙,写作就是一种秘密活动,阅读也是。作家发现艺术的秘密,读者被秘密所震动和感动,皆大欢喜。可是,有些作品写得一览无遗,距离精神的秘密生活要求太远,作家缺少发现,图方便和省事,也就捞不到什么真正长久的好处。
李:是,角度是太重要了,现在中国作家,考虑这个问题的我看很少,坐在那儿,提笔就来了,正着来,拐个弯也不会。
张:你最近读了什么外国小说?
李:《国王的人马》,《追风筝的人》,《我的名字叫红》等。沃伦写的《国王的人马》,写的就是现实,现在,大家都说要反映现实,写反腐什么的,可读一下《国王的人马》,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现实主义?《国王的人马》就是写一个贪官,美国贪官,看人家怎么写?真是写到骨子和灵魂里去了,真是对这个时代人的根本境遇提出了有力的追问。现在,我们的小说,写一个反腐败问题,基本就跟看门老大爷的水平差不多,只是知道一个愤怒。
张:谈一下你对这几部外国小说的理解好吗?
李:《我的名字叫红》,角度也很小,讲十六世纪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宫廷里的一群细密画师,一桩谋杀案,还有说书人。从一个小口子进去,内部又非常丰满,小说就应该针眼儿里走骆驼,从针眼进去,从小角度进去,处理大主题。这小说的主题,涉及到伊斯坦布尔究竟是面向东方还是面向西方?这是土耳其两千年来一直犹豫不定的问题,到现在,他们还在为加入不加入欧盟争论不休,还在考虑土耳其到底是伊斯兰国家还是西方国家?是亚洲还是欧洲?直到现在,这个民族还在为这事闹心呢。处理这样大的一个主题,却从如此的小角度切进去,这是我们做不到做不好的,我们的很多小说家都变成大说家了。
张:大主题就从大处写,想法太直,缺乏缜密独特的思考,好像史诗就要写两百年,写三天生活内容的小说,也可能是史诗,心灵的时间,未必与外部的历史时间是同一个概念。
李:小说还要有经验的充实性,现在的小说都是太轻,作家就只有一个故事,把这个故事推衍出来拉倒。小说的可能性其实蛮多的,我们还没有真正把它的可能性打开。包括你,你不是要写那个“卡奴”什么吗?你要写的这部长篇小说我看了梗概,觉得它的好处是有地方性经验,我们这个时代,通过大众媒体传播出来,都是全球性知识,至少也是全国性知识,有根基,有独特性,有历史渊源的地方性经验和知识被遮蔽掉了,我觉得你要抓住这个地方,把它写准确、写得丰沛。
我最讨厌小说里写什么A城B城,你以为自己真是卡夫卡啦?你要写的到底是哪儿?是上海?北京?或者云南的某个小城,你一定要有个科学的实证态度,我们现在大谈现实主义,但已经把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科学和实证背景忘光了,我们所谓的现实不过是个抽象的现实。科学和实证背景下的艺术原则不仅现实主义用,现代主义一样用,乔伊斯写都柏林,每条街上每个店铺的细节都是准确的。
──这些似乎是无聊的小问题,可是,我觉得现在欠缺的就是这些基本问题的自觉,我们可能连小说家的基本工作方法都没有建立起来,小说家不是这样做的,这样做太轻巧了,到监狱里采访半天,听了一个案子,回来就写,可你看看卡波特是怎么写〈冷血〉的。
张:很多年前我读《冷血》,就很吃惊,吃惊的不只是作品写得好,还有作家杜鲁门□卡波特为写这部作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五年,采访无数人和相关的方方面面,做成了死刑犯的朋友,在执刑前,被死刑犯要求去现场。卡波特自己说,三十万字的作品,涉及到所有人和事的文字,都有可以追查的出处,看了介绍,我倒吸一口冷气。
李:杜鲁门?卡波特写《冷血》,调查研究了五年,他采访的就是一个案子,从一九五六年采访,到一九六一年完成,五年啊,采访了多少人?咱们比比吧,中国作家那么多人写案子,我知道都是去监狱里捞一段就来写。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五年太长了,一年行不行?最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没有,小说的充实性和丰富性,肯定就不行。而且,杜鲁门□卡波特是多浮躁的一个人啊,他原来是生活在纽约,成天混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圈里,跟一帮名媛贵妇鬼混。他是那么一个人,然后跑到西部,在肯塔基州,那个地方很偏僻啊,等于中国上海的某位作家,跑到宁夏去,蹲了五年,所以人家牛逼,不服不行。作家,才情是一回事,但活儿能做到哪一步,是另一回事,人家就是下了功夫,并非侥幸。
(一) (二)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