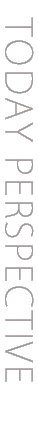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孙行者的筋斗
--“达达”艺术内幕考
王瑞芸
达达还是不必“从政”了,不如还是呆在艺术里,下场还好一点。所以,泰赞拉在艺术上推行的达达倒是被历史流传了下来。苏黎世达达在巴拉离开后,主要由泰赞拉接手,他一方面继续组织达达夜总会的活动,把夜间的表演活动命名为“达达之夜”,在苏黎世不同的地点巡回演出,以扩大达达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在1916年春天出版了达达的杂志,通过杂志把达达向国际输送。达达杂志也象“达达之夜”的表演,上面满是胡言乱语。比如,有海森贝克写的离奇文章“幻想的祈祷者们”,并配有阿尔普的抽象插图。泰赞拉的一篇怪文:“第一次对灭火器先生的精神探索”,被他称为是“词语的拳击赛”。此外,他们四处发信,向各国的文化名人,艺术家们徵稿,然后把徵稿编在一起出版了一本国际评论集,起名为《伏尔泰酒家》,这本集子里收集了不少名人的文章和插图,其中有名诗人阿波里奈尔,画家马瑞尼堤的文字,有毕卡索,莫蒂格里安尼,康定斯基等人的绘画。通过办杂志和出书,达达运动果然蔓延出去,成为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新流派。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麋集在苏黎世的各国流亡者都陆续回国了,泰赞拉的“达达之夜”开始冷清,泰赞拉必须寻求新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是法国的艺术家比卡比亚(Francis Picabia)。
比卡比亚在巴黎艺术界是个头面人物,他不仅在艺术上具有不衰的革新精神,而且在生活上具有放荡不羁,无所不为的做派。他父亲是古巴人,富甲一方。母亲亦出生巴黎有钱人家庭,比卡比亚是这对显赫夫妻唯一的儿子,一个标准的公子哥儿,锦衣玉食,要什么有什么。他长大成人后,很快成为巴黎社交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从巴黎政界的圈子,到文艺精英的沙龙,比卡比亚无一处不熟,他跟巴黎所有有名的画家,音乐家,作家,诗人都有往还……此外,比卡比亚思维活跃,精力过人,因有南美血统,他长得脸庞黛黑,体格健壮,一个硕大的头颅安在宽阔的肩上,几乎省去了脖子,一个人结实得象个石磴子。他狂欢作乐起来,通宵达旦,不知疲倦。富于刺激的事物他无不插手:女人,鸦片,汽车,艺术,名酒,雪茄……他天生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对任何东西都不肯买账,凡是守规矩的人--无论是老规矩,新规矩,都要被他嘲笑,他永远喜欢给事物以不同的外表,给空洞注入全新的内容。他从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不管别人说了什么,他总要和人争论:“是,然而……”“ 不,但是……”这几乎成了他的习惯,成为他的游戏。在现代艺术史上,比卡比亚是最早画抽象画,画机器的画家;他还创办前卫艺术杂志,杜尚那张著名的给《蒙娜丽莎》添胡子的戏作,本来是悄悄儿画了玩的,就是他拿去在杂志上登出来公布于世,后来成为达达艺术的鲜明标识。
这样一个人,肯定该是达达最好的同盟者。泰赞拉甚至在第三期达达杂志上写道:“万岁,比卡比亚,来自纽约的敌对画家!”(因为比卡比亚在纽约创作出了他离经叛道的机器画,)泰赞拉还把比卡比亚出格的现代诗和机器绘画登在达达杂志上,并给他去信约稿,希望他全力支持达达。可巧,
比卡比亚当时不但已经从纽约回欧洲,而且正在瑞士休养。这个衣食无虞,生活放纵的人因为成天过着美酒女人、艺术诗歌的刺激生活,把自己神经弄垮了。他1917年10月从纽约一回到巴黎后,很快陷入了一场恋爱,和一个正在闹离婚的巴黎女子打得火热,他住的公寓里四处是报纸,书籍,高尔夫球棍,滑雪板,非洲面具,航船模型,满地的床垫子--象征着他生活的丰富同时混乱。为了让自己过于劳累的神经休息,他只得去瑞士清静处疗养,他的妻子和情人全追了过去。可是比卡比亚把这些烦恼全抛开,他在疗养处依然作画写诗,并且打算在瑞士的一家画廊开个画展,然而他的那些举世无双的机器画把画廊主吓着了,拒绝接受它们。机灵的泰赞拉得知了消息后,在给比卡比亚的信中提到这件事,并且说,那个画廊主啊,“如果你在他肚子上开一扇门, 你会发现里头满满的全是酒糟。”这一来两个人马上亲热起来,比卡比亚不仅约泰赞拉见面,而且邀他搬到巴黎去,可以住在他有“很多房间”的公寓里。那时他们彼此需要:泰赞拉的确需要挪动了,苏黎世的作用只在战时,战争结束,苏黎世就不热闹了,搞艺术运动,当然还是巴黎。而比卡比亚则正处于中年危机中,他该有的全有,名声,钱,女人,可是他被他的“有”弄得无所适从,他需要和年轻人接触,获得行动的活力。因此他们在苏黎世的见面洽谈甚欢,比卡比亚不仅为泰赞拉的达达杂志提供稿子,而且还鼓动巴黎艺术界的朋友都来援手支持这份杂志。比卡比亚回巴黎后,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催请泰赞拉尽早到巴黎去。这个只图刺激的人觉得,巴黎的日子简直枯燥死了,满世界没有一个有意思的人,只剩下新交的这个朋友和他手中的达达还有点子意思了。
在比卡比亚的连连催促下,泰赞拉终于来到巴黎。可他来的真不是时候。首先,比卡比亚已经不住在那个塞纳河左岸,有“很多房间”的公寓里了,他离开了他的妻子,携情妇在塞纳河右岸另租了个公寓,那个公寓只有一间卧房。1920年1月的某一天,比卡比亚正招待后来成为超现实主义“教父”的普吕东(Anfre Breton)及另外几个年轻朋友在公寓吃饭聊天,聊到兴起时,比卡比亚和普吕东退进卧室继续大谈尼采哲学,把别的客人留在客厅里。不久一个客厅里的朋友闯进卧室,打断他们谈话,比卡比亚生气道:“滚出去!难道一个人就不能有个安静说话的地方?” 那个朋友比他更生气,嚷道:“好上帝啊,你的女人马上要把孩子生在客厅里了!”比卡比亚这才跳起来。在医学院学医的普吕东跳得更快,简直象是被蛇咬了一口似的,他匆忙拿起衣帽忙不迭地告辞脱身。普吕东八成是怕被主人留下来接生,因为他是在场唯一一个医学院本科生,可是他对写诗远比接生要在行,还是赶紧溜的好。
普吕东的担心是多余的,比卡比亚已经预先约请了接生婆。接生婆并不知道要给谁接生,当她来到楼下,认出了比卡比亚的豪华汽车,才吃惊地想起来,这里的男主人就是几个月前请她在左岸的一家公寓里给自己妻子接生的同一人,现在她又被请来为他的另一个女人接生了。她把手抱在一起喃喃叹息说:“艺术家,天哪!瞧瞧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事。”
就在比卡比亚的情妇生下孩子后的不多几天,他公寓的门被敲响了,比卡比亚不在--比卡比亚可不是那种耐烦奶瓶尿布的男人,他早躲出去开车兜风了。敲门进来的是泰赞拉。比卡比亚的女人虽然知道泰赞拉是谁,却没有料到他会这种时候出现,更没有料到他来是打算住下的。她作难道,她刚生了孩子,连比卡比亚也得睡到客厅里去,泰赞拉只能去住旅馆。泰赞拉紧张得快要哭出来,只好告诉她,他没有钱。于是她只能留他住下,让比卡比亚去住旅馆。泰赞拉立刻就在客厅里打开他的行李,他的衣物倒很有限,可是他带来了无数的文件,杂志,通信,打字机……眨眼功夫,比卡比亚的客厅就被泰赞拉布置成了达达总部,泰赞拉照了自己的作息时间忙开了,他编杂志写信弄到深夜,然后睡大半个白天,下午四点才开始早餐。闲下来他就把比卡比亚新得的宝宝抱在臂弯里,边摇着他边说,“说,达达,小东西,说,达达……啊?”就这样,他在那个公寓里直住了好几个月才搬出来。
泰赞拉的确把达达带去了巴黎,他没去之前,他已经被巴黎崇尚革新的艺术青年企盼着了。比如普吕东,因为泰赞拉的达达杂志先于他传入巴黎,他上面写的达达宣言非常投合激进的巴黎年轻人的胃口。泰赞拉没到巴黎前,普吕东也开始跟他通信,信中对他充满崇敬之情,普吕东当时正年轻有为,满世界寻觅出色的人物做榜样,以他对达达的了解,他认定泰赞拉正是他期待着的那种具备优秀思想的精彩人物。泰赞拉感觉得到这一点,当然也就努力配合,让自己的形像能符合巴黎艺术青年们的期待。他把自己说成27岁(其实刚满22岁),并且说他和当时也住在苏黎世的爱因斯坦,荣格等人常有往来。(是吗?) 他还把给普吕东们的信写得曲折诲涩,高深难解……最后当他终于出现在他的巴黎崇拜者前时,他们全愣住了。他们眼前的这个小个子罗马尼亚人和他们在照片上见着的那个打着领带,带着皮手套的形像多么不同啊,他根本象一个矮小的日本人,漆黑的头发,过份苍白的脸色,手脚都很短,溜肩,一双眼睛摇摆不定,好像找不到一个落脚点。
不过,泰赞拉从事活动的热情和机灵还是让巴黎的文艺青年们佩服。不久,泰赞拉和他们一起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组织了一次达达活动,普吕东那批人在巴黎生巴黎长,还不大会胡闹,开头只能规规矩矩地朗诵诗,直到泰赞拉登台,局面才有了转机--让这次活动象个达达的样子:他把一首诗剪开,把那些零碎的词搁在帽子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摸出来读,这才把观众的情绪点燃了,大家都闹起来……这样的活动他们连续搞了几次,泰赞拉希望在巴黎把他们曾在苏黎世做的事继续下去。可是,他没有料到时过境迁,在和平时期,这样的胡闹并不大有市场,根本不可能象当日在苏黎世那样一触即发。在巴黎的每个活动他们要挖空心思设计,制造效果,才可能调动观众情绪。到了黔驴技穷时,他们甚至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他们这些参与者在一张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让主持人抓阄,抓到了谁,这个人就得用左轮枪对着自己脑袋开一枪,左轮枪上六个弹道的轮盘里放上一颗子弹,碰上碰不上听天由命。这当然是太过份了,那些参加者是艺术家,诗人,作家,并不是敢死队员,他们到底给吓住了,只有退出……法国作家纪德当时这么描写巴黎达达组织的活动给他的印象:“我一直期待出现一个更好些的局面,那些达达们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大众没有头脑的愚蠢。可是瞧啊,一些年轻人上了台,手挽着手,严肃,呆板,好像一个合唱团似的宣陈一些空洞无稽之谈,后台有人对他们喊叫:做一两个动作出来。结果惹得人大笑不已。”
我们大约可以想象,达达是什么,达达应该是一个人对于人类那种一本正经,自以为是的愚蠢突然了悟,因此才生出了嘲笑幽默的心情--任何人看见了明显的愚蠢是无法不发笑的。可是,若没有真正看出愚蠢,那就不可能有嘲笑戏谑的心情。显然那些手挽着手上台的年轻人们,未必是开悟之人,他们只不过是应了要求那么做而已:无论他们对人类事务、对人生懂得多少,他们却要努力去符合达达规定的样子,摆出一付嘲弄派头,甚至有人要在后台操纵他们--“做一两个动作”……这的确非常可笑,这让他们几乎象台前的木偶。这一下惹人笑的不是大众现存的愚蠢,而是他们自己表现出的愚蠢了。
总之,泰赞拉想要发动的巴黎达达完全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显然,达达的那种发泄、胡闹,在战争时期非常有效,因为战争一把拉下罩在人们日常价值上的面罩,你想要不看清楚都不行,似乎人人都被战争一棒子敲醒,看见了许多过去没有看见的东西,尤其是生活中流行的许多伪价值。因此苏黎世达达嘲弄现存价值就绝没有后来巴黎年轻人的那种做作成份。而战争一结束,人们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庸常生活的那一层幕布就又落了下来。除非特别有洞察力的人,(比如杜尚),一般的人都会随波逐流,顺势而下,重新生活在老套子里。何况巴黎是个什么地方?巴黎是个重保存,重添加的城市,巴黎人一点都不虚无,他们要结结实实,有模样有品位的东西,达达那种顽童似的胡闹算个什么。事已至此,达达必须出局。
于是,达达运动在巴黎转换成了探索潜意识的超现实主义运动(1924),这是后话。只说到了巴黎后,达达运动也很快分派,一方是比卡比亚,泰赞拉,另一方是后来做成超现实主义领袖的普吕东和他的同志们。这两个派别中的人为了能争做“领导”闹得分道扬镳。普吕东是个特别严肃的人,目的性极强,认准了目标就非达成不可,而且他要求周围的人对他绝对服从。泰赞拉也是个争强好胜,野心勃勃的角色。而比卡比亚更加对谁都不会买账,这些达达们最后搅成一锅粥,弄到不欢而散。
在1923年夏天,泰赞拉再想做一次达达活动的大展示。好容易找到一个俄国人办的剧场作为场地(其他巴黎的剧场不肯接受达达们),这次活动策划是多样化的,有电影(电影当然不是寻常电影,而是达达风格的电影),有诗歌朗诵--请演员来朗诵,上台的人将是最年轻的达达分子。不知道泰赞拉出于什么动机,他居然做了一件非常反达达的事,他让人出去散布说,谁要是来这个活动中蓄意捣乱,他会不客气地把他扔出去(达达,怕人家捣乱?!这象达达吗?那天晚上,普吕东去了,他是自己买票去的,守门的当然认识他,对他说,
行啊,让你进去,可是你得规规矩矩的,别出声。) 开场先是音乐,礼貌地鼓掌,跟着诗人上场,开始念诗,念的是:纪德,死在战场上了,比卡比亚死在战场上了,毕加索死在战场上了……毕加索就在下面正排坐着,抱着胳膊,一声不出,普吕东却跳起来,跳到台上,用手杖指着朗诵的人叫他滚下台去,那个人回嘴,普吕东举起手杖就打,他也打得太重了,一下子打断了人的胳膊。剧场大乱,台上的人忙着救人,普吕东才是个好样的,面无惧色,更无悔意。等把伤员抬走,剧场安静下来, 演出要继续下去,但人们看得到泰赞拉已经叫来了警察,把普吕东已及他的几个党羽指给警察,让警察把他们轰出去。 我们且先不急着去批评普吕东的粗暴做法,只消看看泰赞拉的做法,倒要替他脸红,凭是谁都叫得警察,唯独他不可以,他是什么人,一个达达领导,一个反对社会常轨的领袖,居然要叫警察来帮助维持秩序,只这个行为就可以知道,达达是一落千丈了。就象当年人们在报上评论的那样:他叫人不能原谅的不只是给巴黎抹了黑,而且是给这个世界抹了黑。
这就是达达运动的内幕。明眼人可以看到,这里头可没有杜尚什么事。然而,杜尚至今一直被历史肯定为达达艺术祖师爷一样的人物,至少是达达艺术的首席代表,纽约现代美术馆这一次办的达达大展,目录封面就是杜尚的画了胡子的蒙娜丽莎--达达艺术的经典之作。实际上杜尚不仅当时没有参加达达的任何活动,他那张经典之作,也是在他自己私下里的戏作,作于1919年,是他的朋友比卡比亚看见了拿出去发表出来的,而那时达达运动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此外,杜尚不仅没有参加达达当时的任何展览活动,甚至在达达展览向他征集作品时,拒绝参加。他发了份回绝的电报给达达分子们,一向温文尔雅的杜尚居然在电报上说了句粗话:“给你们个逑!”
杜尚为什么不见好达达,为什么不愿意与他们为伍?因为他看得出达达分子们对于艺术不是真看破,不是真放下。纽约现代美术馆达达大展中的那些艺术家,后来个个都不达达了,个个都重新享受起艺术的种种方便好处了,个个又都重新尊重起艺术来。唯有杜尚一个人,对于艺术的虚伪和造作终其一生给予抵制,终其一生超越在这个伪价值之上。
杜尚是怎么超越的,他超越的意义在哪里?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这里不赘。
(一)(二)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