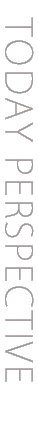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对话: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与长篇小说创作
对话者:朱小如 汪政 李敬泽 洪治纲
一、长篇小说创作: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一个“瓶颈”?
朱小如:比较毕飞宇的《平原》和东西的《后悔录》,我觉得《平原》对毕飞宇的意义更大些。就他个人创作而言,长篇小说是“弱项”,从他第一部《那个夏季那个秋天》到《玉米》系列再到《平原》,生长了近十年才总算有了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其实也不仅仅是毕飞宇一个人的问题,就六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而言,长篇小说创作目前还是一个“瓶颈”阶段,不知各位对此有无同感?尤其相比较他们在中、短篇上所获得的成就,比如鬼子在读他《被雨淋湿的河》之后,我一直期待能读到他的长篇小说;又比如荆歌,长篇写了好几个,但读来总觉得气象不大。当然,我希望能从这样一个粗浅的印象中探讨出某些并非个案性的问题,以便共同思考。
汪政:长篇小说确实是六七十年代很多作家的痛,我是认为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文体是有关系的,在气息上是相通的,是有不少各体皆擅的作家,但更多的作家在文体上是不平衡的,可惜这个简单的道理很少有人能心平气和地看待与接受,相反,倒有不少人在这那儿较劲。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体好像有高下,因为长篇在形制与容量上确实显得丰满巨大,在目前也被市场看好,即以一个简单的事实看,出一部长篇比出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容易多了。反正,许多原因,让我们的作家走着从中短篇到长篇的公式化的路。一个作家似乎不写长篇就算不得作家,不能算成了正果。在许多人眼里,飞宇的中短篇非常棒,谈起他的长篇,就有不过尔尔的感觉。飞宇也是较劲的一个,但较劲各不一样,有的人生来气息与长篇不对,飞宇是幸运的,他找到了那个气息,没有练岔气,从《平原》看,气息调匀了。但这样的幸运者毕竟不多。
洪治纲:从整体上看,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的长篇小说成就并不是非常突出,至少没有他们的中短篇那样获得应有的艺术高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近些年来,他们开始普遍地潜心于长篇小说创作,并拿出了一些具有超越性的作品,如李洱的《花腔》、林白的《万物花开》、艾伟的《爱人同志》、东西的《后悔录》、毕飞宇的《平原》、张生的《十年灯》等,都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读这些作品,我非常欣喜地看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进行清醒的自我超越,而且每一个人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平原》我就不谈了。像林白的《万物花开》,就从很大层面上突破了作者的个人经验,将叙事全面渗透到层底生活的还原之中,既展示了林白的想象能力和写实能力,又保留了她所独有的灵性气质。艾伟的《爱人同志》在表现历史意志与个人关系时,非常突出地展示了个人命运与内心理想的分裂状态,以及人物在这种分裂状态中艰难抗争的过程。而《后悔录》通过“如果”的假设,让一个人在后悔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曾广贤之所以不停地后悔、懊丧、愤懑、积郁,以至于在“后悔大全”里生活了半辈子,除了自我省察的内心表达之外,他显然还想从精神上寻找某些自我突破的方式。因为后悔不只是一种本能的心理活动,它还带有某种理性的反思意味。随着曾广贤的不断后悔,以及在后悔中的自我反思,东西终于揭开了隐藏在“后悔”背后的生存困境——在那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以“仓库”作为集体意志演变的特定符号,通过仓库功能的不断变化所折射出来的权力历史、价值观念、社会伦理的变迁,也看到了在这种变迁之中个人命运的沉浮。兰德曼说,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社会的存在。正因如此,曾广贤的每一次后悔,其背后都负载着沉重的历史沉疴。它们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存在。
当然,与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及一些老作家相比,他们的长篇总体上看似还有些单薄,涵盖历史的深度与广度似乎不够,但是,他们却显示了自身特有的叙事智慧以及对人性的深度发掘。长篇创作不同于中短篇,丰厚的人生积累、娴熟的叙事技艺、深邃的思想内蕴以及漫长的叙事耐力都是缺一不可的,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在面对长篇写作时,可能需要更好地整合自身的各种写作优势,在写作速度上再放缓一些,应该会出现更有价值的作品。因此,如果说有“瓶颈”,我觉得对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来说,这种“瓶颈”主要在于确立“伟大的中国小说”意识,调整自己的写作资源,强化内在的思想力度,放慢自己的写作速度。
李敬泽:是瓶子就总会有颈,问题首先是你得成为一个瓶子。
长篇的根本问题是世界观问题,就是你怎么看世界,怎么想象世界。我赞同汪政的说法,长篇不是要写便写的。鲁迅没写长篇,人们很遗憾,但我看鲁迅没写是他的明智,他的气质、他对世界的想象方式都是非长篇的;同样,博尔赫斯也写不了长篇,他索性宣布长篇是冗长的废话,对他那种近乎厌食症的写作来说,长篇确实是一种夸张的暴饮暴食。
长篇不是一个字数问题,长篇涉及一套对世界的假设,比如,我们相信,世界和人生不是由杂乱无章的片断构成,我们相信世界和人生自有其意义,而且在一个行动与时间的结构中展现出来;我们相信自己是在讲述一个重大的人类故事,否则就很难理解你为什么费那么大劲去写它,也就是说,你得相信这里边有命运、有英雄和受难者、有诉诸所有人的重要情感和困境,等等。
总之,长篇是要从“信”出发,如果不信那就没有写长篇的必要。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信?这对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是个问题,他们是习惯性的怀疑主义者,就天性而言,他们可能更擅长把整体拆成碎片,而不是想象和虚构一个整体;他们还习惯性地认为自己很有思想——一种令情感休克的机智,他们拒绝对世界做出任何总体性言说,似乎这样就会玷污他们的思想贞洁,而如果我们不肯领会总体性的力量,我们当然无从领会命运。这一切加到一起,就有治纲说的“单薄”问题、广度深度问题、叙事耐力问题等等,也就是说,在相当程度上,他们的长篇写作是从不信长篇开始的,这当然会有巨大困难,恐怕也不是单凭“努力”就能够解决。
二、童年记忆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长篇叙事资源
朱小如:很久以前,我曾与敬泽讨论时,谈到了长篇小说故事情节的“自然长度”、人物性格塑造的复杂性和整体性、以及“泥沙俱下”的繁复审美特点;同时也谈到了六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大多起步于“成长”记忆。如东西的第一部长篇《耳光响亮》、艾伟的《越野赛跑》,这次毕飞宇的《平原》也还是如此。汪政说《平原》不似“伤痕”胜似“伤痕”,我基本同意,因为在我读来,《平原》渗透出来的远不仅仅是对“文革”的历时性影响,而更多地隐含了毕飞宇对“城乡”共时性的深层次思考。我愿意拿毕飞宇笔下的“端方”这个人物和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作比较。“端方”逃离乡村的意识、方法与“高加林”的意识、方法恰巧相反, “高加林”对土地的反叛和批判要比“端方”理直气壮的多(与其说路遥是受当时思想解放意识形态影响所致,还不如说是受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影响所致)。而“端方”对土地的反叛和批判却比“高加林”显得胆怯且理由不那么充分。这不仅仅是“端方”面对的土地比“高加林”面对的土地“肥沃”的问题,而是“端方”面对的土地恰巧正是当初“城市”、“知青”不得不接受的“再教育”的扎根之地。“端方”(也可以直接说是毕飞宇)自然不具备对如此“神圣土地”的坚定反叛和批判意识。因此,我觉得把“端方”这个人物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人物图谱中来仔细考察,一定十分有意思。当然也包括“吴蔓玲”这个超越了“知青文学”领域的独特的“知青”形象。
尤其是如果把“端方”以及“吴蔓玲”看作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或许就恰恰点中了毕飞宇潜意识流露到笔下的“城”和“乡”,谁要强行改造谁都只能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结果。也难怪治纲要说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里,无论是热血的下乡知青“吴蔓玲”还是“端方”那样出生在乡村的青年在“成长”的路上都找不到适合自身的奔跑方向。但是,毕飞宇果真只是将《平原》局限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果真只是仅仅停留在叙述一个有关“文革”的“成长”记忆故事吗?我愿意追问的是《平原》对当下社会的投影或者用套话来说就是《平原》的现实意义究竟何在?同时我也更想追问的“成长”记忆究竟给了毕飞宇这一代作家内心以及一生怎样的影响?
洪治纲:小如的看法很有意思。“文革记忆”确实是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一个重要的叙事资源。面对这场历史劫难,虽然表现的作品已经很多,但是,似乎并没有出现具有经典意味的优秀之作。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在书写文革记忆时,主要是突出了一种少年叙事视角和成长过程中人性被扭曲的惨痛情形,像《平原》、《耳光响亮》、《越野赛跑》,包括王彪的《越跑越远》、刘庆的《长势喜人》等,都是如此。至于他们在作品中所隐含的人物逃离乡土的愿望,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逃离乡土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共同理想,或者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因为人的生存意志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乡村百姓普遍看不到命运的亮光,而城市虽然也不见得有多好,但多少会带给他们一些希望,一些物质上的慰藉。二是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普遍处于青春成长期,特有的理想冲动、生命热情和极度闭塞的生存环境构成了极为尖锐的冲突,使他们在展望人生蓝图的过程中,不得不通过逃离、奔突来安顿自己的青春理想。这种情形在《平原》中的端方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但是,我更看重的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在书写文革记忆时的那种迷惘感。他们对历史意志所构成的极为惨烈的场景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而是更多地书写那种青春期的骚动和迷惘,奔突和游离,狂野和破坏。像《后悔录》、《越野赛跑》、《长势喜人》等作品,对此都有出色的表现。这些作品都明显地超越了以往的知青小说,并赋予了人物以特有的浪漫气息和诗性意味。
朱小如:在读毕飞宇的《平原》之前,我以为有关“文革”的“成长”记忆故事写得最完整的是王刚的《英格力士》、有关“知青”的是都梁的《血色浪漫》,因为两者都完成了由“成长”到“成熟”的过程,完成了由“记忆”以往而“总结”一生的精神升华。同时两者也都让我们清晰地读出了作品对当下现实社会生活的强烈观照。
在我读《英格力士》时感觉王刚可能也是六十年代出生的,当然还需要敬泽来证实。
李敬泽:王刚不是。
朱小如:小说里正面描绘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英语教师王亚军。来自上海的他平时爱涂香水,喜欢单独给女生补课,处处与文革时期的新疆生活文化环境格格不入。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小知识分子,在屈辱中凸显出与众不同的“智识”给了学生刘爱成长过程中以巨大的影响。用小说里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单纯的绅士式的“英格力士”精神,《英格力士》中的英语教师王亚军身上具有的“智识”和他所处的那个普遍反智时代的矛盾冲突,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地域的差异来抹平,其关键还是城乡文明的基本价值观不同。所以敬泽说他从《英格力士》里读到的是久违的内心“柔软”。用“柔软”一词来观照当下现实社会生活中被打磨得“僵硬”了的人心,的确再准确不过了。
但是《平原》呢?敬择似乎选择了更内心化的观照,是因为“平原”相对“高山”无话可说,亦或是因为无论是“成长”到“成熟”,还是“记忆”以往而“总结”一生,最终发现“他(即便是已经“逃离”了土地的中国人)的心里、身体里依然伸展着那个广大的平原”。所以,毕飞宇这一代作家和路遥那一代作家的精神家园依然不是在城里,而是“宿命”般地停留在王家庄。而李洱在坚持了数十年的知识分子写作后也回到了《石榴树上结樱桃》上,不能不说也有某种关联。
汪政:敬泽从意象切入《平原》是有道理的,不能把《平原》分得太清楚,一清楚,有意味的东西就会被忽略、删除。毕飞宇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对流行、对模式、对众多既成话语的反拨,它是成长,但却超越了个人,它是文革,但却并不将其置于中心,它出乎了人们对这部小说的众多想象,企图还原那个时代真实而丰富的生活,唤起人们快要遗忘的记忆,它告诉人们,在文革时期,不仅仅是文革。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不能以政治中心来代替自己的视角,不能用重大事件取代日常生活。
洪治纲:童年生活对一个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像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夫卡、胡安?鲁尔福等等,可以说,童年记忆对他们的创作都产生了极深的影响。这种影响,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会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即使是他们后来并不在故乡而是在其它地方生活和写作,这种童年记忆好像也始终没有被抛弃。尤其是他们幼年时代生活过的那种地域文化风情,那种民间的语言和形象,都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影子,好像这是无法改变的。从余华的作品中,我们也同样能感觉到那种柔软而又潮湿的江南小城的味道。
我曾就这一问题与余华进行过讨论。他认为,童年生活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选择,没有第二或第三种选择的可能。因为一个人的童年,给你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是一个人和这个世界的一生的关系的基础。我们从母亲的子宫里出来以后,面对这个世界,慢慢地看到了天空,看到了房子,看到了树,看到了各种各样我们的同类,然后别人会告诉我们这是天空,这是房子……这就是最早来到一个人的内心中并构成那个世界的图画。今后你可能会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认识,但是你的基础是不会改变的;你对人和社会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但你对人的最起码的看法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最根本的连接,谁也没法改变。所以,他曾说:“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我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童年记忆正是文革记忆,只不过有的在乡村,有的在城市,它们构成了作家们对世界的最初认识,也形成了他们处理生活的最基本的方式。所以,他们即使不写文革记忆,不写他们最初生活的情形,但他们作品中的许多背景和人文环境,也脱离不了童年的记忆。或许,这就是兰德曼所说的“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吧。
汪政:一个人的出生年代与他的叙事资源的关系非常复杂,从理论上讲,作家出生的年代当然决定了人直接的经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其他途径获取资源。李大卫的长篇《集梦爱好者》就非常奇特,他更多的是超越共时经验的想象。其实,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他们心智真正成熟并以文学的眼光看取生活大都已经是七十年代末了,但是奇怪的是,大部分作家对他们的少年生活,特别是文革非常执着,这是一个情结。在读《平原》时,我特别指出飞宇对文革的别一种书写,因为即使在文革,政治也不是唯一的,日常生活还在,小传统还在。我的意思是,第一,除了文革,我们可写的还有许多;第二,对文革时代,我们也应有新的视角。对中国作家,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作家来说,这种文革情结值得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上做深入的分析,社会对一个人,一个群体,乃至对所有成员在记忆上的强迫到底有多大的力量?
(一)(二)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