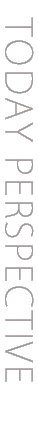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整体困顿 局部开花
──2007年小说综评
邵燕君
“时代大书”落入败境 “个人化历史”显露生机
本年度几位著名作家推出的“时代大书”都落入了令人心痛的败境。
张炜的《刺猬歌》试图以丰饶的“民间想象”, 重述山东半岛海边丛林小镇棘窝镇百年来的历史。在“齐文化”怪诞神秘的气息中夹杂着强烈的时代情绪,这情绪来自对当下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但这不满的表达,仍像作家当年介入“人文精神论争”时一样,仅表现为立场和姿态,未能深入到理性批判的层面。于是,一股灼热的激情转化为愤怒,整个作品陷入狂乱的想象。
格非的《山河入梦》是继《人面桃花》之后又一部反思历史的作品,这一次面对的是中国五十年代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然而,作家对乌托邦社会的理解和想象和完全是简单化的,思想资源没有超出大众常识的水准,对一些政治规则和潜规则的描述甚至低于常识水准。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先锋小说”代表人物之一的格非,文字能力竟突然滑至大众读物的层次,人物也相当漫画化——这都不禁让人想起余华的《兄弟》。莫非“先锋作家”在将注意力重新转向“写什么”,转向“对历史现实发起正面强攻”之后,无法驾驭的题材将他们多年来训练出的“怎么写”的技艺也一并压垮了?
这一类作品中,最令人失望的还是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作为当代最具“理论素养”的作家之一,王安忆直书“文革”前期一代青年的思想启蒙史,自然引人翘首以待。然而,这部以“时代”为题目、以“启蒙”为主题的小说却未能抓住那个时代的精神实质,小说的实际落脚点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身革命家庭的子弟如何被“小资情调”启蒙——王安忆再次告诉我们“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在寻找时代对话的基点上,她显然回避了我们这个时代与启蒙时代有关的核心问题,如专制-民主、物质-精神、革命-告别革命,而是顺应了消费主义的大众观念,将《启蒙时代》写成《长恨歌》的“特别阶段史”。更令人沮丧的是,进入到小说,又完全感受不到《长恨歌》式的世俗烟火气,当然,更缺乏《叔叔的故事》中那种思想的激情。小说充斥着连篇累牍的议论和辩论,却缺乏理性的穿透力。加之形象模糊、情感隔膜、语句冗长,完全成为一个封闭的闷局。近年来批评界对王安忆创作“不冒险”、“理念化”等倾向有诸多诟病,这些病象在这部作品中显得越发严重。
这两年的“长篇热”中,有“史诗化”追求的不在少数,但都在思想支撑点上出现问题。这或许在提醒我们思考,在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解体后,文学上“宏大叙事”是否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个人角度进入历史的方式就特别值得关注。
林白的《致一九七五》从时间上看像是《启蒙时代》的后续,写的是“后革命时代”的故事。不过,这里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边缘小镇的普通女孩,她没机会读到什么“黄皮书”内参,也没听说过什么“地下沙龙”。她随着“大流儿”学工学农,又随着“大流儿”上山下乡。于是,她不必承担什么时代使命,特定的年代只是她个人成长的环境背景。获得“历史的解脱”后,林白充分依赖身体的记忆,味觉、嗅觉、听觉,如万物花开。经过《一个人的战争》的自我言说和《妇女闲聊录》的彻底倾听后,林白的身体插上记忆的翅膀深入历史,而这段公共的历史也以林白的方式被打开。然而,在“个人化写作”和“个人化历史”之间,林白似乎还没有把握好分寸和界限,尤其是第一部,时代即使作为环境背景都没有得到有效烘托,不免令人疑惑,如此个人的记忆何必冠以“致一九七五”这样的时代命名?什么样的个人记忆才有资格承担历史叙述?
韩东的《英特迈往》也是一部“个人化历史”,故事从1969年一直讲到2005年,试图通过几个人的命运勾勒出几许时代的样貌。不过,相对于林白的作品,这篇小说在经验和语言上都缺乏足够的个性穿透力,叙述似乎一直在故事表层滑行,“零度回忆”的节制平淡中也多少显出无精打采,这也是韩东从《扎根》延续下来的长篇叙述风格。
长篇立意形式上的新探索
本年度,有几部长篇小说在形式上有新尝试。李锐和蒋韵夫妇合作的《人间》是“重述神话”系列在中国继苏童《碧奴》、叶兆言《后羿》之后出版的第三本小说。其故事原型是在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白蛇传”。较之前两部的意义虚浮、想象贫弱,《人间》无论在立意上还是在技法上都进行了有创意的翻新,在原有的故事原型基础上,选取了“身分认同焦虑”这样的现代性命题,结构上采取多线并进的架构,又与古典的“悲情”气韵连通,使小说在保有中国古典伦理和情怀的基础上具有了现代精神,这正是“重述神话”的意义。
刁斗的《代号:SBS》更是一部颇有实验性的小说,它以一个商业间谍的故事为架构,借用侦探小说的元素,同时吸收多种当代大众文化形式,创造了一个卡夫卡《城堡》、奥威尔《一九八四》式的当代公司社会的存在寓言。小说写得相当有趣,但不乏严肃性,虽然还有混杂粗硬之嫌,却不失为一种有拓进性的尝试。
相对于这两部小说,朱辉的《天知道》和麦家的《风声》的特色则限于在“纯文学”和通俗小说间寻求平衡。前几年在有关“纯文学”反思的讨论中,就有人建议“纯文学”吸收一些通俗小说形式要素以增加可读性。这种尝试的难点在于如何在借鉴通俗形式的同时保持“纯文学”的特性,这显然也是朱辉在小说中着重把握的,可惜目前的平衡结果尚不理想。由热播电视剧前导、乘“主旋律”而来的《风声》,更适合以文化研究的方式讨论。单从叙述形式上看,它主要继承了先锋小说叙述策略并同时借鉴包括“杀人游戏”在内的通俗叙述方式,而对后者的运用显然比前者要出神入化。相对于以前的中篇小说,麦家在语言上有明显退化,电视剧脚本的痕迹随处可见。
此外,还有几部长篇值得关注。董立勃的《白麦》和张者的《桃花》分别是其前作《白豆》、《桃李》的续作,题材和风格都没有什么变化,但质量有所下滑。李佩甫的《等等灵魂》以商战故事为题材,虽流畅好看,但比起《羊的门》那样深入传达“中原文化”的小说,作家对商业灵魂的把握还不够深透。池莉封笔几年后推出的《所以》写她熟悉的婚恋题材,本来引人期待,然小说空洞无物、矫揉造作,语言也粗糙得难以卒读,是本年度“名家新作”中让人特别失望的一部。相比之下,盛可以的《道德颂》也写一个婚外恋的老套故事,在结构、人物处理上还有明显毛病,但感情充沛,语言凌厉,自有其可观之处。来自科尔沁草原的作家千夫长的《长调》,以平实而悠长的笔调书写草原的记忆,在近两年来众多草原题材小说中算颇为出色的一部。
中短篇:现代形态小说颇具规模
本年度中短篇最令人振奋的是,出现了一批艺术上相当成熟的现代形态小说佳作。主要有:李浩《一只叫芭比的狗》(《花城》2006年第6期,短篇)、王威廉《非法入住》(《大家》第1期,中篇)、七格《真理与意义——标题取自Donald Davidson同名著作》(《山花》第6期,中篇)、黄咏梅《暖死亡》(《十月》第3期,中篇)、艾伟《小偷》(《收获》第6期,短篇),张静《珍珠》(《西湖》第2期,短篇)等。
中国当代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形式变革以来,超越现实主义、向现代形态小说发展一直是“纯文学”的进军方向。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当代创作面临的最尴尬处境在于,大多数作家对现实主义没有吃透,“画蛋”的功夫远没过关,向现代主义奔跑的脚步必然踉跄。其结果是,不少追求创新的作品两头不靠,理念和现实“两层皮”。不但虚矫,而且虚弱。不仅难懂,也确实难看。所谓“先锋”的大旗下长久汇集这样一些“伪先锋”的作品,难免让人丧失信心。
在这样的格局下,这些现代形态小说佳作较具规模地出现令人重振信心。看得出来,这些作家都深受国外现代大师的影响,不过这影响不再是外部模仿,而是内部生根。那些遥远的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如存在感、荒谬感、幽暗罪恶的人性,都有了本土的生长语境。特别可贵的是,作家们具有了“以实写虚”的功夫,小说不再只是“意念的行走”,而是落实到细节,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如此的进展,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现代主义二十年来的持续影响,同时也不可忽视作家们长期坚持之功。写作这些作品的作家虽已不算年轻但都尚属“文学新人”之列,多年来他们偏居一隅,埋头苦干,不但抗拒着“常规写作”的诱惑和挤压,甚至在“纯文学”的理念被逐步掏空为一种“不及物”的代名词时,仍固守着其纯粹性:技艺的完美和精神的先锋。为其如此,才能在文学整体下滑的大势下,在局部创新处获得沉稳的推进。
曹乃谦小说引人关注
本年度一直名不见经传的曹乃谦成为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其主要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作品被相继出版(《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4月;此前还有《最后的村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12月)——这自然与马悦然先生的力推盛赞有直接关系(马悦然称:“曹乃谦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不管中国大陆的评论家对曹乃谦的看法……,我觉得曹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中国评论界虽然不必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首是瞻,但也不必由此产生逆反心理,还是应该在对其创作精读细研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
既然说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评价和定位,尤其是提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就必须把曹乃谦置于几类相关作家——包括与其题材、体裁、风格相近的当代作家(如李锐,特别是与《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同期创作的《厚土》)、文学史前辈作家(如也使用“晋方言”的“山药蛋派”代表作家赵树理)、世界级的优秀作家(如同样用一系列精短短篇书写一个特定人群的前苏联作家巴别尔的《骑兵军》)——的比较中来考察。在如此苛刻的品评中,我们看到,曹乃谦的创作虽然极具特色并在多方面有探索成果,但比起在该方面最有突破的作家而言,还是略逊一筹。而且,以“最一流的作家”的标准来衡量,曹乃谦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作品主题过于单一(一句“食色,性也”完全可以概括),手法也相对单调,缺乏足够的深厚性和丰富性。
尽管如此,曹乃谦仍不失为一位极具特色的作家,他对方言的全方位运用、对小说对话功能的开掘、对“留白”的嗜好,对语言近乎吝啬的精简,都令人叹服。在那么漫长的寂寞岁月里,他固守着自己的园地和耕种的方式,在当代众多随风而动、面相模糊的作家中,风光独具,堪称优秀。曹乃谦的被“发现”不仅对文学史有补遗之功,对日益松弛芜杂的当下创作也是一个有益的警示。
“底层文学”深入乡土
在贾平凹、孙慧芬等作家以长篇的方式将“乡土文学”推向“底层”的同时,近几年来持续发展的“底层文学”也进一步深入乡村,从“底层”的角度表现当下农村的生活状态和变化。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曹征路《豆选事件》(《上海文学》第6期,中篇)、胡学文《淋湿的翅膀》(《十月》第3期,中篇)、罗伟章《最后一课》(《当代》第2期,中篇)、存文学:《人间烟火》(《收获》第3期,中篇)、范小青《父亲还在渔隐街》(《山花》第5期,短篇),等等。
《豆选事件》是曹征路“底层写作”中的又一力作。小说选择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豆选事件。豆选,显然不仅仅是乡村基层选举的一个讨巧的说法,这个源自于延安革命政权的民主形式似乎联系着某种传统和某一乌托邦。即便从最表层的修辞看来,“金豆豆,银豆豆,投在好人碗里头”,这一民主形态上的轻松或许已经构成了今天乡村民主进程的一次反讽:与革命圣地的艳阳天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今天基层选举的实践举步为艰,而每一次有效的选举几乎必然是一次动荡、一次事件,一次革命的献祭。
从《那儿》到《霓虹》到《豆选事件》,曹征路关注“底层”的笔触,由城市到乡村,由工人到农民。感人的依然是作家对底层民众现实困境和历史成因的深切体认和同情,动人的依旧是弱势者在被逼到绝境后反抗力量的积聚和爆发。虽然不像《那儿》那样荡气回肠,《豆选事件》在语言和叙述结构上更为讲究,加之题材的拓展,使曹征路的“底层写作”在总体上更上一层楼,而其与文学史上左翼文学的关系,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的话题。
在目前的“底层写作”中,范小青的写法是最“轻”的。《父亲还在渔隐街》乍一看像是写农民工进城后“留守子女”的问题,而竟然被写得颇有些先锋的意思。范小青其实讲述的是关于追寻与迷失的故事,她将我们面对现代生活的滚滚红尘时那种无尽的茫然与恐慌表达得委婉多致,叫人恍惚。“底层文学”兴起后,大都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笔法,像范小青这样基本只是以“底层”为题材、将之带入自己原有风格的写作,可以在写法上开拓路径。
“成熟作家”推陈出新 “期刊新人”稳扎稳打
成熟作家的中短篇佳作本应是每年最令人心安的收获,但这两年的“收成”都不好。不过,还是能精选出的几篇——迟子建《福翩翩》(《人民文学》第1期,中篇)、苏童《为什么我们家没有电灯》(《收获》第5期,短篇)、韩少功《末日》(《山花》第10期,短篇),这些小说都保持了作家一贯的风格和水准,值得细看。
相对于这些“守成之作”,毕飞宇本年度推出的两个短篇《相爱的日子》(《人民文学》第5期,短篇)和《家事》(《钟山》第5期,短篇)则颇有新意。小说在取材上抓住了当代生活的新质,“发现”了变动时代的“新伦理”。《相爱的日子》从性与爱的夹缝入手,写处于城市边缘、缺乏资本又向往婚姻的两个年轻人,在“临时”的关系中如何“性”爱。《家事》采用当下中学生自成一统的话语方式,写这些由独生子女构成的“新新人类”,如何在彼此间建立模拟的亲属关系,如何“换种语言说爱你”。虽然与作家原本擅长的题材和风格相比,这些小说在经验的把握上恐怕还不够深透,艺术上似乎也不够圆熟,但如此的新变,显示了一个成熟作家的开放性,令人兴味颇浓。
发现、培养、推介新人一直是文学期刊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里本来有一套很完整的新人培养机制,《萌芽》、《青年文学》、《鸭绿江》等都是专门发表新人作品的刊物。各大期刊的编辑也向以发现、培养新人为责、为能、为荣,这是一项优秀的“伯乐传统”。这些年来在市场的压力下,尤其在“80后”称霸市场、走上文坛的过程中,期刊的势力一度处于下风。不过,随着“80后”明星在市场上的潮起潮落,这套机制和这项传统的力量再次显示出来。
自2007年全面改版、以新锐气象令文坛侧目的《西湖》杂志,一年来每期以大量篇幅推举新人,成为继《山花》之后又一个重要的新人培养基地。该杂志举办的首届“西湖.中国新锐小说奖”是一个典型的“期刊新人”奖——评委由多家主流文学期刊和选刊负责人组成,候选作品也来自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文学期刊。三位获奖作家——徐则臣(大奖,获奖作品《跑步穿过中关村》发表于《收获》2006年第6期)、笛安(提名奖,获奖作品《莉莉》发表于《钟山》2007年第1期)、张静(提名奖,获奖作品《珍珠》《有情郎》发表于《西湖》2007年第2期)——可以被视为主流期刊认可的“期刊新人”的代表。
在三位获奖作家中,大奖获得者徐则臣是资格最“老”的。自2004年以《啊,北京》等“京漂小说”露出头角以来,徐则臣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写作势头。几乎在获奖同时,他的五个中篇(《苍声》《伞兵和卖油郎》《把脸拉下》《水边书》《还乡记》)和一个长篇(《夜火车》)分别在《收获》、《十月》、《上海文学》、《当代》、《作家.长篇》发表,篇篇铆足了劲,显示出一个“实力派”新锐作家的全面爆发。如果说上年度的《跑步穿过中关村》显示其“京漂系列”进一步走向成熟的话,本年度的《苍声》则显示其另一向度的创作——“花街系列”向“文革”这样的具体历史背景挺进,少年的记忆在时代残酷和人性恶的炼火中捶打,年轻作家的笔力也在“苍声”中完成“成人礼”。
2005年,张静以处女作《采阴采阳》登上文坛。她鲜活真切的生活经验、缠绵而不乏锐利的笔致,以及对于现代都市中包括女性之间新型关系的入微呈现,使这篇小说不但当时让人眼前一亮,过后仍久久难忘。张静的小说很有“现代感”,如果说在《采阴采阳》中“现代感”还主要体现在内容,在《珍珠》中则体现为形式。小说借用一个卡夫卡《变形记》式的突变,打开了日常生活外壳下的裂隙,虽然笔力尚且嫌弱,但圆润凝练,荒诞的故事框架里,细节触手可摸。小说后附的创作谈,言语机智,见地不俗,形象呼之欲出,也可当小说来读。张静出生在70年代最后一年,如按照这些年文坛盛行的“代际划分”方式推举新人,恐怕难免落得“遗珠”的命运。而作为一个幸运的新人,张静自“冒出头”后,产量也并不高。不过,《珍珠》的质量让人放心。希望在这个新人“辈”出的时代,她能像珍珠一样,静静地生长,熠熠生辉。
在三位获奖作家中,笛安是唯一的“80后”作家,而在“80后”作家中,笛安一向算是比较低调的。她迄今发表的作品在同辈作家中并不算多,但都很有分量。两个中篇曾被列为杂志头条(《姐姐的丛林》,《收获》2003年第1期;《莉莉》,《钟山》2007年第1期),两个长篇也颇具影响(《告别天堂》,《收获.增刊》2004年秋冬卷,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芙蓉如面柳如眉》,《收获.长篇专号》2006年春夏卷,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5月版)。在这几部作品中,除了被春风社列入“星计划”主打书的《芙蓉如面柳如眉》更凭想象力推演以外,其余三部全部是直面青春的体验。对于成长的隐秘,她不回避、不逃离,不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也不大惊小怪自恋自怜,而是以一个成长者的庄重恳切,投入而又沉静地书写着。这种正面、直接的写作方式,在“80后”作家中是难得的。《莉莉》是一个“80后”式的童话,又是一部成长小说,那葆含着生命元气的成长之痛,打通了代际之间的隔膜,使作品饱满新鲜、明媚动人,既呈现出不同于前辈作家作品的新质,又能被文学传统所接纳认同。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年一度对文学的回顾总是以名家起,以新人止。不管名家的表现是否尽如人意,只要新人尚怀新锐之气,我们对文学就保有信心。
(本文为《北大选本.2007中国小说》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该选本由“北京大学当代最新小说点评论坛”编选、点评。更多点评文字见“北大评刊”网站http://www.pkupk.com)
(一)(二)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