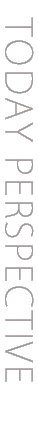 |
|
 |
《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
|
|
|
“重画”世界华语文学版图?
——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
郜元宝
这是丰富的文学史知识与相对单薄的论述对象之间另一种严重不对称,以及这种不对称必然导致的文学史谱系错认。读王君的评论,中文系学生可以学到不少中外文学史知识点,可以随着王君的妙手牵引,在中外著名作家(名单可以无穷放大)和两岸四地以及北美二十位当代中青年华语作家之间,目不转睛地滑来滑去。除此之外,对这二十位作家具体的创作情境和文学贡献,应该不会知道太多罢?
我列举上述两种严重不对称,丝毫没有一面恭维王君理论造诣和文学史功底一面奚落其批评才具的意思。在论述七位大陆地区当代作家时,王君仍然能够冲破自己手造的理论围困和文学史迷宫,克服理障,直指本心,精到地点出他们的成败利钝。比如他认为“王安忆并不是出色的文体家。她的句法冗长杂沓,不够精谨;她的意象视野流于浮露平板;她的人物造型也太易显出感伤的倾向。这些问题,在中短篇小说里,尤易显现”,他还断言在《长恨歌》中,“张爱玲小说的贵族气至此悉由市井风格所取代”。光这两点如果成立,就完全可以在张爱玲和王安忆之间划下一道鸿沟,怎么到头来王还是成了张的嫡传?就算王果然得到张的“教外别传”,也不一定能说“海派作家,又见传人”。张氏固然自称“到底是上海人”,但彼之上海和30年代的“海派”已经是两回事。又比如,在论述李锐《无风之树》时,王君敏锐发现,“《无风之树》的角色多有第一人称现身说法的机会。惟独苦根儿的章节,由叙述者从旁代言。李锐对这一角色的刻画及嘲讽,用心良多。”他进而认为前一种方式“优点是凸显大小人物的主体性,然而重复运用,也容易暴露作者刻意求工的痕迹,反而显得造作------生动的叙述不仅止于对人物话语的模拟”。这不仅揭示了《无风之树》的主要问题,也关联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物说话和隐含作者叙述因为知识分子身份变迁而频频发生的主客错位,以及李锐在现代汉语众多资源中偏执于方言口语的误区。可惜王君于此吃紧处轻轻滑过,也许他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锐“激发了两种美学立场——壮美(sublime)与丑怪(grotesque)——对峙”,又接续了从叶圣陶《倪焕之》开始的“对于启蒙理念及教育方法的省思”,也就是呼应了王君的理论预设和庞大的文学史架构,故尔百俊遮一丑,甚至丑也变得俊俏非凡了。
众多的现代哲学与批评理论,丰富的中外文学史知识,帮助王君完成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先验“座架”。这个“座架”绝对凌驾于具体文学现象,后者永远是无休止地填补这个吞噬一切的“座架”的材料,不可能在此“座架”之外拥有自己的意义。在这一点上,王君实在以其学者的迂阔压抑了他作为一个批评家的真实感受。
另外,王君著此大书,其自觉担当的使命也过于沉重:一是要对他心目中的“跨世纪华文文学版图”进行“扩大”和“重画”,二是要竭力证明“跨世纪华文文学”不仅没有衰歇之兆,反而足称“世纪末的华丽”。
为完成第一项使命,王君反对把当今华文文学理解为“以大陆为中心所辐射而出的文学的总称”,主张“去中心化”,将原本作为“祖国文学的延伸”的“世界华文文学”翻转为没有中心的“众声喧哗”,故此不仅在作家选择上13比7十分自然,更重要的是,一旦如他所说,跨越了以往“中央与边缘、正统与延异的对比”,进入“众声喧哗”的新格局,新的对话场域便“于焉而兴”(无非就是“去中心”的“众声喧哗”)。职是之故,他不得不竭力扩张当代华语文学未必能扯上关系的理论阐释空间,不得不竭力扩张当代华语文学未必真正拥有的中外文学史背景。这样做的好处是:在众多理论交错“旅行”中,在无限放大的文学史寥廓空间,确实很容易人为制造想象的“众声喧哗”。
但“两岸四地文学”真实的时空关系以及所存在的问题,也就不必牢心费力地阐述了。
比如,过去的“大陆中心”构架现在还有没有残留的合理性(无论从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还是从文化传统与国民根性上看)?如没有,那么这种构架是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失效的?导致这种传统构架失效的动力是什么?世界华语文学在不同地区固然有不同的问题乃至表述这些问题时仰仗的王君所谓“中州正韵”之外的不同“方言”,但如果把“中州正韵”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包括大陆地区“当代文学”传统的复杂共生,那么“中州正韵”之外,“两岸四地”的“方言”还能找到另外的精神文化资源吗?如果确实有另外的资源,其力量又足以摧毁“中州正韵”的霸权,那么这种新资源究竟是什么?“两岸四地”多数不通外语的华文作家汲取这种新资源的渠道和能力又当如何解释?在“两岸四地”华语作家当中,王君能找到拥有新资源而足以摆脱“中州正韵”从而顺利进入另一种文化空间的理想人选吗?如果有这样的人选,那他还属于“跨世纪华语文学”吗?他身处异质文化空间,还会继续使用中文来写作吗?为什么王君在竭力摆脱“中州正韵”的过程中,实际上反而屡屡借助“中州正韵”的背景作支援,甚至将台、港、星马和北美地区许多华文作家屡屡编织到“五四”新文学传统中去呢?这不是很矛盾吗?如果说,“中州正韵”只是在顾彬教授所说的铁屋子里畸形发展的“当代文学”特有的奴隶语言,那么它的狭隘的奴性与奴性的自觉,它的奴隶式的焦虑、戏拟、反抗、颠覆、破坏或王君很喜欢说的“内爆”,不也可圈可点吗?它在捆绑桎梏中锻炼出来的易简严谨的文体,与港、台、星马等地华语作家往往跳跃、杂沓、松散如豆腐渣的中文,不也形成可供分析的一种有趣对照吗?那种豆腐渣式的中文,是“中州正韵”的“花果飘零”(唐君毅语)、散席流珍呢,还是“中州正韵”与新的语言文化资源在后殖民背景下交媾而成的怪胎,这不也是需要正面回答的问题吗?
王君如果真想“扩大”、“重画”其“跨世纪华文文学的版图”,应该直面以上这些根本而困难的问题。在当今华语文学研究界,解答这些根本而困难的问题,对两岸四地及北美华人世界都比较了解的王君,应该算是上佳人选,但王君没有做他该做的,只是大施障眼法,偷换概念,转移论题,以“扩大”、“重画”中外批评理论的版图并乱构中外文学史谱系,来代替对世界华语文学版图切实的“扩大”与“重画”。
为完成第二项使命,也就是为了竭力显明华语文学“世纪末的华丽”,王君的文学批评只好严格局限于理论爆炸、标签乱舞以及中外文学史的家谱指认,而一味回避对所论作家的优劣判断。即使碰到不得不作价值评判时,也迅速转移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上述“王安忆论”和“李锐论”就是著例。王君只管分析作家“写什么”与“怎么写”,以此为跳板,攀缘理论高点,指认文学史谱系,告诉读者在他所提供的理论高点与文学史谱系共同组建的先验“座架”中,作家作品可能享有的位置,而不负责交代作家实际上“写得怎样”。一触及后一个问题,就很不利于他的“世纪末的华丽”了。
因为“众声喧哗”,故有“世纪末的华丽”;因是“世纪末的华丽”,必然“众声喧哗”。这种简捷方便的循环论证就是王君所依靠的两个最大理论预设——很不幸,我觉得也成了妨害他尽情发挥批评家才具的两根讨厌的绳索。
似乎有必要补充说明:入选的“当代小说二十家”以及王君经常提及或准备日后作专论的残雪、林白、阎连科等,都属于尖新谲怪之类,都喜欢大写“情色”、“暴力”、“耽美”、“变态”、“怪异”、“奇谭”、“扭曲”、“恋师”、“恋尸”、“食尸”、“腐朽”、“酗酒”、“排泄”、“茅房”、“口腔期症候群”、“自渎”、“饕餮”、“拾骨”、“丑闻”、“窥秘”、“淫猥”、“同志”、“乱伦”、“阉割”、“射精”、“膻色腥”。王君所欲“扩大”、“重画”的“跨世纪华文文学的版图”,原来是如此“华丽”。
不肯直面世界华文文学存在的问题,只一味证明世界华文文学迎来了它的“世纪末的华丽”,这种“我们其实很好”的说辞,是否有点身处西方强势国家的被殖民者容易养成的自卑/自傲心理?“耽美”于一部分华文作家的尖新谲怪,萃取奇特而刊落平常,是否暴露了被殖民者希望引人注目的心态,并显示其作为另一种身份的殖民者荣归故里、反身对母语文学的他者化认知?
不管怎样,“跨世纪华文文学”经过王君“扩大”与“重画”,差不多只剩下鲁迅所谓“奇特的(grotesque),色情的(erotic)东西”了 。鲁迅很早就意识到,“奇特”和“色情”是欧美一些文艺家在落后国家与地区热衷探寻的,现在却于王君书中意外得之,岂不痛哉。
2007年3月7日
(一)(二)
|
|
|
|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